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
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婚姻家庭關系,即婚姻家庭關系的主體一方或雙方是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引起婚姻家庭關系產生、變更或消滅的法律事實發生在國外。一般認為,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范圍包括涉外婚姻的成立及效力、涉外夫妻關系、涉外離婚的條件與效力、涉外父母子女關系及其他家庭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涉外婚姻家庭的數量逐年上升,涉外婚姻家庭糾紛也不斷增多。其中,涉外離婚及親子關系案件是涉外婚姻家庭案件的主要類型。我國現行立法僅對涉外結婚、離婚、扶養、監護做出籠統規定,內容不夠全面,已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正如有學者指出,我國現行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的規定存在“五不”現象:即不系統、不全面、不具體、不明確、不科學。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個最重要、最根本、最可行的途徑就是加快制定統一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1}。目前,《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立法已經啟動,草案正在醞釀之中。[1]在《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中,如何設計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法的內容,是國際私法學界和實務界共同思考的課題。學界普遍認為,應采用比較國別國際私法的方法,對其他國家現行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進行梳理和歸納,借鑒國際社會最新立法經驗,以完善我國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適用法。本文結合正在起草的《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草案)第六章的相關規定進行探討。
一、涉外結婚的法律適用
關于涉外結婚的法律適用問題,《民法通則》第14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外國人結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即中國公民與外國人結婚的實質條件和形式要件,均適用婚姻締結地的法律。對涉外結婚的效力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188條規定:“適用婚姻締結地的法律”。上述規定存在主體不周延的問題,不能解決現實生活中所有類型的涉外結婚。現實中,涉外婚姻的類型除了中國公民與外國人結婚之外,還包括外國人之間在中國結婚,以及中國人之間在外國結婚等情形。因此,補充和完善涉外結婚的法律適用規則是司法實踐的迫切需要。
提交全國人大法工委討論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第61條規定:“結婚的實質條件和效力,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在境外締結的合法婚姻,但當事人故意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定的除外。”第62條規定:“結婚形式符合婚姻締結地法律,或者符合當事人一方的本國法律、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的,均為有效。具有同一國籍或者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結婚,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由其所屬國領事依照其所屬國法律辦理結婚。”上述規定涉及涉外結婚的4個問題:(1)結婚的實質要件的法律適用;(2)結婚的形式要件的法律適用;(3)境外締結婚姻效力的承認;(4)領事婚姻。與現行立法相比,上述規定彌補了不足,涵蓋涉外結婚的所有問題,但仍然存在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一是將婚姻的實質要件與婚姻的效力兩個不同的法律問題置于同一條款中,在邏輯上欠妥。婚姻的實質條件是決定婚姻是否成立問題,而婚姻的效力則是婚姻成立后能否引起預期的法律后果,即其有效性能否得到承認。[2]從立法的科學性看,宜將婚姻的成立與婚姻的效力以兩款分別作出規定。同時,對境外締結婚姻效力的承認問題,是以“法律規避”制度來限制,還是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來把關也值得探討。二是領事婚姻的適用條件。從各國適用領事婚姻制度的條件來看,一般要求結婚雙方都是領事派遣國的僑民。上述第61條的規定允許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在中國締結領事婚姻,這在實踐中存在困難。例如,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在中國結婚,那么是由美國領事按照美國法來辦理結婚,還是由法國領事按照法國法來辦理結婚呢?實踐中,對于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結婚,必須適用中國法律,即婚姻締結地法律。因此,辦理領事婚姻的條件需要進一步明確。
未來立法應在總結現行法律運行效果的基礎上,結合國際社會的立法趨勢,對涉外結婚涉及的上述4個問題分別作出規定。
(一)結婚實質要件的法律適用
對于結婚的實質要件,國際社會普遍以“婚姻締結地法”作為首要的準據法,這在國內立法和國際公約中都有體現。以婚姻締結地法為基本規則的國家有美國、澳大利亞、南非以及阿根廷、智利等拉丁美洲國家{2}。1978年海牙《婚姻締結和承認婚姻有效公約》(1991年5月1日生效)第2條規定:“婚姻的締結,適用婚姻締結地國家的法律。”婚姻的實質要件適用婚姻締結地法是一項最基本的法律適用原則。當然,也有一些國家為了實現促進婚姻有效的實體政策,采用選擇性沖突規則,婚姻符合“婚姻舉行地法,或者當事人一方的本國法”的,均被認為有效。[3]我國現行立法也堅持對所有類型的涉外結婚都適用婚姻締結地法的原則。該原則簡便易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運行效果良好。因此,我國應采納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保持現行立法的連貫性,對涉外結婚實質要件采用單一雙邊沖突規范,直接規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而無需采用選擇性沖突規范。即“結婚的實質要件,適用婚姻締結地法。”
(二)結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適用
結婚形式要件主要是結婚的外在形式問題,為了確保婚姻的有效性,一般采取寬松的規定{3}。但也有一些宗教信仰濃厚的國家對涉外結婚的形式要件要求嚴格,對于本國公民與外國人結婚,如果沒有按照其本國法規定的宗教習慣或儀式舉行結婚,該婚姻的效力將得不到其本國的承認,從而產生所謂的“跛腳婚姻”。[4]為了盡可能避免“跛腳婚姻”現象,目前國際社會對跨國婚姻的形式要件一般都持寬松態度,主張盡量使婚姻在形式上有效。在涉外結婚形式要件方面,或者采用婚姻舉行地法,或者采用當事人的屬人法。其中,結婚的形式要件適用婚姻締結地法是一項被廣泛接受的法律適用規則,得到大多數國家立法的肯定,并被1978年海牙《婚姻締結和承認婚姻有效公約》第2條采納。只是一些國家區分在內國締結的婚姻和在外國締結的婚姻,對前者只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后者則可以選擇適用婚姻締結地法或當事人的屬人法。如日本2007年修訂的《法律適用通則法》第24條規定:“(一)婚姻的成立,對于各當事人,依其本國法。(二)婚姻的方式,依婚姻舉行地法。(三)盡管有前款規定,婚姻符合一方當事人本國法的方式,為有效。但婚姻在日本舉行,一方當事人為日本人時,不在此限。”
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區分涉外結婚的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統一適用“婚姻締結地法”。為了避免“跛腳婚姻”,《草案》區分涉外結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并對涉外結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適用采取寬松態度,以無條件選擇性沖突規范加以規定。只要婚姻符合婚姻締結地法、婚姻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本國法、住所地法或經常居所地法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為有效的,該婚姻形式要件即為有效。《草案》這一規定是可取的。但為保持屬人法在整個涉外婚姻家庭關系中適用的一致性[5],應對《草案》規定的準據法順序稍作調整,具體如下:“結婚的形式要件,符合下列法律之一者,均為有效:(一)婚姻締結地法;(二)當事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三)當事人的本國法。”
(三)婚姻效力的承認
婚姻效力的承認主要是對在境外締結婚姻的有效性的認可。一項在外國締結的婚姻是否能夠被內國承認為有效,一般要對婚姻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進行審查后加以確認。關于婚姻效力的認定,國際社會一般也是“依婚姻締結地法”。1978年海牙《婚姻締結和承認婚姻有效公約》就規定了由婚姻締結地法決定婚姻的有效性,但違反承認國的公共政策除外(公約第9條)。不管婚姻締結地國家是否屬于公約的締約國,凡是在婚姻締結地有效成立的婚姻,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是有效的,其效力在任何國家都應得到承認。除非有相反證據證明,否則婚姻締結地主管機關頒發的婚姻證書是有效的。(第10條)當然,如果婚姻效力的承認明顯違反被請求國的公共政策,或違反被請求國關于結婚的根本性實質要件(第11條),則可以拒絕承認該婚姻的效力。[6]
《意見》第188條規定“認定婚姻的效力,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與上述海牙公約規定的精神基本一致,但并沒有采取限制措施。《草案》第61條第2款也堅持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原則,同時以“法律規避制度”來拒絕承認外國締結婚姻的有效性。針對實踐中當事人雙方規避我國強制性規定到境外結婚(主要是法定婚齡),或國際社會出現的同性婚姻現象,對其效力加以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但以法律規避制度來拒絕承認外國締結婚姻的效力,并不能達到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目的,也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當事人的利益。試舉例說明:中國公民甲男,21周歲,在英國留學期間與19周歲的英國乙女相戀準備結婚,雙方本要在中國結婚,但知道自己沒有達到我國婚姻法規定的法定婚齡這一強制性規定,因而選擇到日本結婚,并按照日本法律締結合法婚姻。對此婚姻的效力是否予以承認?若按照《草案》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在境外締結的合法婚姻,但當事人故意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定的除外”則此婚姻的效力不被認可。顯然,拒絕承認該婚姻的效力,既沒有達到維護我國社會公共秩序的目的,也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再如,荷蘭公民甲男與乙男在荷蘭依據荷蘭2001年《注冊伙伴關系法》登記為同性婚姻。甲、乙在中國上海某跨國公司工作,現申請中國承認其同性婚姻關系。甲、乙雙方的同性婚姻在荷蘭(境外)屬于合法的婚姻,也不存在故意規避我國婚姻法中的禁止性或強制性規定,如果以上述“法律規避”制度是不能拒絕承認其效力的。但對于這類同性婚姻,如果承認其效力,將明顯違背我國的社會公共秩序。因此我國應拒絕承認這類婚姻的效力。在涉外結婚問題上,如何達到既維護我國社會公共秩序,又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利益的立法目的?筆者認為,應采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因為,國際私法中的法律規避制度是防止涉外當事人利用一國沖突規范而惡意規避內國實體法中的強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規范的法律機制,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功能和目的都存在不同{4}。在國際私法理論上,限制外國法的適用主要是通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來實現。為解決“移住婚姻”或稱“遷移婚姻”,一些國家也是通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來否定規避法律的婚姻的效力。[7]1978年海牙《婚姻締結和承認婚姻有效公約》第9條也允許締約國對境外締結的違反本國“公共秩序”的婚姻的效力拒絕承認。實際上,1997年民政部辦公廳《關于對中國公民的境外婚姻證件認證問題的復函》中也規定,“當事人依婚姻締結地法律結婚,只要不違背我國婚姻法的基本原則和社會公共利益,其婚姻關系在中國境內有效。”因此,我國應采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來拒絕承認外國締結的婚姻的效力,而不是通過法律規避制度來否定。未來立法可以規定:“婚姻效力的認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但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締結婚姻的效力,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社會公共利益。”
(四)領事婚姻
領事婚姻是指在駐在國不反對的情況下,一國駐國外的領事或外交代表按照本國法所規定的方式,為本國人成立婚姻的制度{5}。領事婚姻制度得到1963年《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和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肯定。但領事婚姻的有效性一般取決于以下三個條件:一是駐在國表示同意或不加反對;二是申請結婚的當事人具有派遣國國籍,即派遣國領事只能為本國人辦理結婚[8];三是按照領事派遣國的法律所規定的方式辦理結婚。由于領事婚姻是由一國授權的駐外領事辦理的結婚,因此在派遣國和駐在國都屬有效。從我國的實踐來看,1983年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國務院僑辦聯合發出《關于駐外使領館處理華僑婚姻問題的若干規定》指出,“申請結婚的男女雙方均是華僑,且符合我國婚姻法的規定,如駐在國法律允許,雙方又堅持要我使領館為其辦理結婚登記的,我使領館可為其辦理結婚登記。若駐在國法律不承認外國使領館辦理結婚登記的效力或該結婚申請不符合我婚姻法關于結婚的規定,則我使領館不宜受理。華僑與外國人(包括外籍華人)申請結婚登記,我使領館不得受理。”1997年民政部辦公廳《關于對中國公民的境外婚姻證件認證問題的復函》中規定,“兩個在國外長期學習、工作、探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華僑除外)在國外結婚,原則上應在中國駐該國使、領館辦理結婚登記(居住國不承認的除外)。”可見,我國使領館辦理領事婚姻,要求男女雙方都是中國公民。與此對等,對于外國駐華使領館辦理領事婚姻,一般也要求雙方當事人都是使領館所屬國的國民。實踐中,對于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在我國結婚,一般要求其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辦理結婚登記,目前還沒有出現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在中國辦理領事婚姻的情形。為此,關于領事婚姻可作如下規定:“具有同一國籍的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結婚,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由其所屬國領事依照其所屬國法律辦理結婚。”
二、涉外夫妻關系的法律適用
夫妻關系是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配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包括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民法通則》沒有專門規定涉外夫妻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但在司法實踐中,《意見》第188條和第189條都是處理涉外夫妻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意見》第188條規定:“中國法院受理的涉外離婚案件,離婚的原因以及因離婚引起的財產分割問題,適用我國法律。”因此,對于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離婚案件,其夫妻財產關系也適用中國婚姻法處理。而根據《意見》第189條規定,涉外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適用與被扶養人有最密切聯系國家的法律。
《草案》第63條規定:“夫妻人身關系,適用其共同本國法律;無共同國籍的,適用其共同住所地法律;無共同住所的,適用其共同經常居住地法律;無共同經常居住地的,適用其婚姻締結地法律或者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該條采用有條件選擇性沖突規范,以夫妻共同屬人法(包括共同本國法和共同住所地法)作為支配夫妻人身關系的主要準據法,在沒有夫妻共同屬人法存在時,則以婚姻締結地法和法院地法作為補充。這一規定表明我國對涉外夫妻人身關系的法律適用采取從嚴控制的立法精神。但夫妻人身關系作為一種典型的身份問題,在沒有夫妻共同屬人法存在的情形下,應適用“婚姻締結地法或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還是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對此應作進一步探討。
《草案》第64條規定:“夫妻財產關系,適用當事人協商一致以明示方式選擇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適用前條的規定;但涉及不動產的,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該規定將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引入涉外夫妻財產關系,當事人可以“明示”方式自由選擇支配其財產關系的準據法。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情況下,依次適用當事人的共同本國法、共同住所地法、共同經常居住地法;如果當事人沒有共同屬人法,則由法院選擇適用婚姻締結地法或法院地法。至于不動產的歸屬問題,無論當事人選擇法律與否,都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涉外夫妻財產關系十分復雜,如何適用法律解決其財產歸屬,不僅涉及當事人的權利,還關系到保護正當的交易秩序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對此,《草案》的規定顯然考慮不足,不僅對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沒有作任何限定,也沒有對雙方就夫妻財產制所選擇的法律對第三人的效力問題加以規定。
未來立法應對涉外夫妻關系的法律適用做出更為細致的規定。
(一)夫妻人身關系的法律適用
夫妻人身關系作為一種身份關系,由當事人的屬人法來支配是國際社會普遍遵守的規則。《草案》關于夫妻人身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是可取的。但正如前文所述,同一法律中屬人法的適用順序應保持一致。從現行立法來看,除了法人屬人法是指其本國法之外,我國對屬人法的理解主要是住所地法。從目前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住所地法代表了屬人法的發展方向,這一趨勢在夫妻關系領域應予以強化{3}160。從司法實踐來看,以當事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為其屬人法,更能體現當事人與特定法律關系之間的最密切聯系。因此,我國對屬人法采用住所地法優先更為適宜。對于涉外夫妻人身關系,首先適用當事人的共同住所地法。同時,共同住所地法與共同經常居住地法應當作為同一適用順序,兩者是選擇適用的關系,而不應是先后適用的關系。其次,如果當事人雙方沒有共同的國籍或住所,可以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國家的法律。“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現代法律選擇的基本原則,已得到很多國家立法的承認。在夫妻人身關系問題上,不適用當事人的屬人法時,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應適用的法律,既反映了準據法與婚姻之間的實質聯系,也便于法院的司法操作。我國也可以采用這一規則。為此,建議作如下規定:“夫妻人身關系,適用其雙方共同住所地法或其共同經常居住地法;無共同住所或經常居住地的,適用其共同的本國法;無共同國籍的,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二)夫妻財產關系的法律適用
與夫妻人身關系的身份性質不同,夫妻財產關系的契約性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由此,一些國家的立法將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引入涉外夫妻財產制領域。被視為現代國際私法立法典范的《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53條規定:“夫妻財產制適用配偶雙方選擇的法律;法律選擇以書面協議形式,并可以變更選擇的法律;雙方只能在共同住所地法或一方的本國法中做出選擇(第52條)。雙方未選擇法律時,則適用配偶雙方共同住所地法或其共同本國法;沒有共同住所、也無共同國籍,則適用瑞士法。”{6}2004年《比利時國際私法典》也規定,婚姻財產制首先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該法第49條規定:“婚姻財產制適用配偶雙方選擇的法律。配偶雙方只能選擇下列法律之一:(1)配偶雙方在婚姻締結后將設立第一個慣常居所的國家的法律;(2)在選擇法律時配偶中一方有慣常居所的國家的法律;(3)在選擇法律時配偶中一方的本國法。”第51條則規定,“配偶雙方沒有作出法律選擇的,婚姻財產只受下列法律支配:(1)配偶雙方在結婚后均首次設立慣常居所的國家的法律;(2)如果未在同一國家均有慣常居所,依婚姻締結時配偶雙方具有共同國籍的國家的法律;(3)在其它情況下,依婚姻締結地國家的法律。”{7}2007年《日本法律適用通則法》對夫妻財產制首先適用夫妻人身關系的規則,也可以適用配偶雙方以明示的方式選擇的法律,夫妻可以在其一方的本國法、經常居所地法中進行選擇。對于不動產的夫妻財產制,則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而當適用外國法時,對于在日本進行的法律行為及在日本的財產,不能對抗善意第三者,此時應適用日本法{8}。從國際社會的立法趨勢來看,一般都要求當事人選擇的法律必須與婚姻有實際聯系。這些有實際聯系的法律包括當事人的本國法、住所地法、慣常居所地法、財產地法等等。
在國際立法方面,1978年海牙《夫妻財產制的法律適用公約》對夫妻財產制的法律適用規則作了詳細的規定:夫妻雙方在婚前可以在其任何一方的本國法、任何一方有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結婚后夫妻一方首次設立新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中,指定一個法律適用于他們的夫妻財產制(第3條)。如果夫妻雙方在婚前沒有就夫妻財產制指定準據法,則適用夫妻婚后設立第一個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但雙方沒有在同一個國家設立其第一個慣常居所或者締約國聲明必須適用夫妻共同本國法時,則應適用夫妻雙方的共同本國法;如果沒有共同慣常居所,也沒有共同國籍,則應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第4條)。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可以重新選擇夫妻財產制的準據法,但只能在任何一方的本國法或任何一方的慣常居所地法中進行選擇,所選擇的法律適用于夫妻雙方的全部財產。但不管夫妻在婚前還是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選擇夫妻財產制的準據法,都不影響就不動產的全部或部分單獨指定應適用的法律(第6條)。夫妻選擇的準據法一直適用于夫妻財產關系,除非重新指定了準據法。夫妻雙方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采用書面的形式,將其全部財產置于新的法律支配,但不能影響第三人的權利(第8條)。夫妻雙方指定法律應以“明示條款”,或在婚姻合同中表述。關于夫妻財產制對夫妻雙方以及第三人的效力問題,應由公約規定的夫妻財產制的準據法來支配(第9條)。
上述立法表明,對于夫妻財產關系,首先應適用夫妻雙方以明示的方式選擇的法律,選擇的法律必須與婚姻有實際聯系;在沒有選擇法律時,則一般適用夫妻的共同本國法或共同慣常居所地法。我國立法應借鑒上述規定。為保護財產交易的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我國應就夫妻財產制對第三人的效力規定法律適用規則。因此,建議我國涉外夫妻財產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作如下規定:“夫妻財產關系,適用當事人協商一致以明示方式在下列法律中選擇的法律:(一)夫妻雙方共同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二)夫妻一方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三)夫妻雙方共同的本國法;(四)夫妻一方的本國法。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前兩款的規定涉及不動產的,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夫妻財產關系對夫妻雙方以及第三人的效力,依照夫妻財產關系所適用的法律。”
三、涉外離婚的法律適用
涉外離婚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涉外離婚的條件,即涉外離婚的標準或原因;二是涉外離婚的效力,即涉外離婚有效性的承認。《民法通則》第147條規定:“離婚,適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從法理上理解,該條規定的適用范圍應包括離婚的條件和離婚的效力。為進一步明確該規定的適用范圍,《意見》第188條規定:“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離婚案件,離婚以及因離婚而引起的財產分割,適用我國法律。”這一司法解釋是將我國法院審理國內離婚案件的司法模式運用到涉外離婚案件之中。[9]這與國際上通行的離婚訴訟的標的僅限于解除配偶身份關系顯然存所不同。夫妻財產分割應屬于夫妻財產關系的范疇。夫妻財產關系是調整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歸屬問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關系。只有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制的夫妻離婚時才存在夫妻財產分割問題。如果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或約定財產制,在離婚時都不涉及夫妻財產分割的問題。
《草案》第62條規定:“離婚的條件和效力,適用起訴時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當事人協議離婚的,適用其以明示方式選擇的當事人一方或者共同的本國法律、住所地法律、經常居住地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適用離婚登記機關或者其他主管機關所在地法律。”《草案》將涉外離婚區分訴訟離婚和協議離婚。對于訴訟離婚的條件和效力,適用起訴時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即把離婚的準據法界定為“起訴時”的法院所在地國家的法律。該規定不僅明確了離婚準據法的適用范圍包括離婚的條件(是否準許離婚)和離婚的效力(離婚的有效性),而且解決了離婚準據法的時際沖突問題。對于當事人協議離婚的,法律允許當事人就離婚應適用的法律作出選擇。但當事人選擇法律是有限制的:首先,選擇的方式必須是“明示”,即以明確的書面協議約定所適用的法律;其次,選擇的法律必須與婚姻有實際聯系,即當事人只能在一方或雙方的共同本國法、一方或雙方的共同住所地法、一方或雙方的經常居住地法中選擇適用。如果協議離婚的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那么就適用辦理離婚的機關所在地國家的法律。與現行立法相比,《草案》將離婚的條件和離婚的效力均置于“起訴時”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支配,增加了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并將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引入離婚領域。這一規定在當今國際社會尚屬首例,可以稱為中國的超前立法,但并不可取。
關于涉外離婚能否采用協議離婚方式,筆者認為不宜采用。一方面,由于協議離婚方式并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因此協議離婚的效力一般不能得到外國的承認。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國內法上允許協議離婚的大陸法系國家,也不主張涉外離婚的當事人采取協議離婚的方式。新近頒布或修訂的國際私法立法中,一般沒有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條款,更沒有將離婚的準據法完全交給當事人自由選擇的例證。從維護當事人的權益和確保離婚的有效性得到承認的角度出發,我國不宜允許涉外離婚采用協議離婚方式,因而沒有必要單獨規定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
那么,我國涉外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應如何制定呢?與離婚的實體法各國存在巨大差異一樣,各國關于離婚的沖突規范也存在嚴重分歧。概括來說,國際社會關于離婚的法律適用主要有以下規則:①適用法院地法;②適用當事人屬人法;③選擇或重疊適用當事人屬人法和法院地法;④適用有利于實現離婚的法律{9}。從國際社會立法趨勢來看,離婚自由是離婚實體法的發展方向。在此政策的指導下,大陸法國家也在對本國法規則進行改造,通過選擇性沖突規則和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運用,達到實現“離婚自由”的政策目標{3}124-131。例如1986年《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7條、1995年《意大利國際私法》第31條第2款等都采用選擇性沖突規則,以體現促進有利于離婚的實體政策。在普通法國家,法院地法規則一直得到堅持,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并不考慮有關外國法的規定,只是通過擴大法院對離婚案件的管轄權,從而使法院地的離婚法有更多的適用機會。我國現行立法對涉外離婚也采用“法院地法規則”。從司法實踐來看,該原則能夠很好地解決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離婚糾紛,運行效果良好。《草案》延續了我國現行立法精神,以“法院地法”作為涉外離婚的準據法。同時,對涉外離婚的規定更加具體,明確涉外離婚的條件及效力均適用“起訴時”的法院地法。這一規定不僅反映了離婚與法院地國家的公共秩序密切相關的特點,而且還解決了離婚準據法的時際沖突問題。從維護法律的穩定性來看,《草案》的規定值得肯定。為此,筆者建議,未來立法應取消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將涉外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規定如下:“離婚的條件和效力,適用起訴時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四、涉外親子關系的法律適用
親子關系也稱父母子女關系,是指父母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包括自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和擬制血親的父母子女關系。父母子女關系是家庭法領域最復雜的權利義務關系,其核心內容是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及財產進行保護。在國內家庭法上,親子法的內容一般應包括親子關系的成立和親子間的權利義務。因此,涉外父母子女關系也應從上述兩方面制定法律適用規則。
(一)親子關系的成立
涉外親子關系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出生和收養。我國缺乏認定親子關系的實體規范,對因出生引起的親子關系的確認缺乏明確的規定。這一立法意識也直接影響到涉外親子關系確認的立法。至于涉外收養,現行立法僅對外國人在中國收養子女的問題作出單邊規定。無論是《收養法》第21條,還是《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第3條,其適用范圍僅限于外國人在中國收養子女,并規定涉外收養關系的成立,重疊適用中國法和收養人住所地法。[10]資料顯示,我國是跨國收養兒童的主要來源國。目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等17個國家與中國建立收養合作關系。[11]為更好地保護在國外生活的中國兒童的利益,2005年我國已加入1993年海牙《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該公約為跨國收養兒童規定了程序及締約國之間的合作義務,成為我國處理跨國收養兒童的法律依據之一。
在涉外親子關系成立的法律適用方面,《草案》規定了非婚生子女的認領和收養的法律適用規則。《草案》第67條規定:“非婚生子女的認領,適用認領時認領人或者被認領人的本國法律、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中有利于認領成立的法律。”非婚生子女是指在合法婚姻之外所生的子女。[12]隨著“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普及和推行,消除對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歧視成為許多國家親子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一些國家如德國取消了非婚生子女的準正(Claim system)制度[13],但非婚生子女的認領制度仍存在于一些國家的家庭法中。鑒于非婚生子女認領所形成的是人身關系,因此《草案》采納適用當事人屬人法這一系屬,同時堅持對非婚生兒童有利的原則。在認領人和被認領人的本國法、住所地法、經常居住地法中,選擇適用有利于認領成立的法律。對于涉外收養問題,《草案》第68條規定:“收養的成立,適用收養時收養人和被收養人各自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收養的效力,適用收養時收養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收養終止,適用收養時被收養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或者適用受理解除收養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從字面理解,收養的成立,分別適用各自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即收養人的條件要符合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的規定,被收養人的條件符合被收養人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的規定。這與現行涉外收養成立必須同時符合“被收養人住所地法(我國法)與收養人住所地法”相比,明顯放松了涉外收養的成立條件。至于收養的效力和終止,均采用選擇適用收養成立時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如果通過法院終止收養關系,還可以適用受理案件的法院地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外收養問題上,《草案》完全拋棄了適用當事人的本國法,收養的成立、效力及終止均適用收養時當事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所地法。
關于涉外親子關系的成立,未來立法應就親子關系的認定確立一般的法律適用規則,并對收養的法律適用規則加以完善。
1.親子關系認定的法律適用
因出生而成立的親子關系包括婚生父母子女關系和非婚生父母子女關系。實踐中確認親子關系案件既包括非婚生子女的認領問題,也包括婚姻關系中所生的子女的親子關系確認問題。因此,對于因出生而成立的親子關系,我國應從廣義上規定其法律適用規則。即在立法上明確涉外親子關系認定的一般法律適用規則,而不專門限定為非婚生子女的認領。這不僅符合消除對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歧視,最大限度保護兒童利益的原則,也符合現實社會生活的需要。許多國家的立法也都對親子關系的認定規定了單獨的沖突規則。如1988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68條規定:“親子關系的成立、確認和否認,適用子女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如果父母中任何一方在子女的慣常居所地國家均沒有住所,且父母和子女具有同一國家的國籍,則應適用其共同本國法。”2004年《比利時國際私法典》第62條規定:“父母身份的確立,適用子女出生時父母的本國法;如果父母身份的確立源于一個自愿行為,則適用該行為實施時父母的本國法。”第63條規定:“親子關系的準據法的適用范圍包括:確立親子關系的請求權的形式、確立親子關系的舉證責任和證明要素、親子關系的身份條件及后果、提起訴訟的期限。”《突尼斯國際私法典》第52條則規定:“法官應在下列法律中選擇適用對成立有關兒童的親子關系最有利的法律:(1)被告的本國法或住所地法;(2)兒童的本國法或住所地法。”《立陶宛共和國國際私法》第1.31條也規定:“親子關系的確定,在對子女最有利的法律的前提下,適用子女出生時的本國法、住所地法、父母一方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從“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出發,將“最有利原則”適用于親子關系的認定應是未來立法的趨勢。因此,建議我國立法將非婚生子女認領的法律適用規則,修改為確認親子關系的一般法律適用規則,規定:“親子關系的確定,適用下列法律中有利于親子關系成立的法律:(一)子女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二)子女出生時的本國法;(三)父母一方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
2.涉外收養的法律適用
從國際社會立法來看,涉外收養的法律適用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收養的條件;二是收養的效力。對于收養的條件和效力,各國規定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般都以收養成立時當事人的屬人法為其準據法,或適用當事人的本國法,或適用當事人的慣常住所地法。例如,《比利時國際私法》第67條規定,“收養的條件,適用收養人在收養關系建立時的本國法,或收養關系建立時收養夫婦具有相同國籍的國家的法律。收養人無國籍時,適用建立收養關系時均有慣常居所的國家的法律,如果沒有共同慣常居所,則適用比利時法。如果適用外國法明顯更大地損害被收養人的利益,且收養人或被收養人與比利時明顯存在緊密聯系,則適用比利時法。”《突尼斯國際私法典》第53條規定:“收養的要件,由收養人和被收養人各自的屬人法支配。收養的效力,由收養人的本國法支配。具有相同國籍的配偶為共同收養的,收養的效力由共同住所地法支配。”《立陶宛國際私法》第1.33條規定:“收養子女,適用子女的固定住所地國法。收養的效力,適用收養父母的固定住所地法。”跨國收養兒童是以有利于被收養兒童的成長為目標,以兒童最大利益為原則,因此,我國涉外收養的立法應充分考慮對被收養兒童利益的保護。鑒于中國是涉外收養兒童的主要來源國,現行立法規定“涉外收養的成立,重疊適用被收養人住所地法和收養人住所地法”能夠更有利于保護被收養人的利益。《草案》采取適用各自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的做法并不妥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涉外收養成立的法律適用規則較好地解決了我國涉外收養問題,因此應予保留。對于涉外收養的效力,鑒于收養關系成立后,被收養兒童要在收養人所在國生活,所以收養人所在國法律對收養效力的規定直接決定收養人對被收養兒童的權利與義務。因此《草案》規定適用“收養時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為保護被收養兒童的利益,解除不利于被收養兒童成長的跨國收養關系應得到法律確認。實際生活中,因單方面解除或終止跨國收養關系損害被收養兒童利益的事件常有發生。為此《草案》增加收養終止的法律適用規則十分必要,《草案》對收養效力和收養終止的法律適用規則是可取的。綜上,關于涉外收養的法律適用,可作如下規定:“收養的成立,適用收養時收養人和被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收養的效力,適用收養時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收養的終止,適用收養時被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或者適用受理解除收養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二)親子間的權利與義務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規定了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及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這些權利義務被統稱為“親權”(parental power,大陸法國家采用)、“監護”(custody,英美法國家采用),或“父母責任”(parental responsibility,歐盟及海牙公約采用)。一般認為,親權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對于未成年子女以教養保護為目的的權利義務的集合。親權是一種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屬于父母的專屬權,由父母共同行使。而在英美法中,親權與監護不分,都稱之為監護{10}。無論是親權制度,還是監護制度,父母對子女人身方面的權利一般包括:(1)住所指定權;(2)子女被誘拐時的返還請求權;(3)職業許可權;(4)法定代理權;(5)子女身份行為及事項的同意權{11}。而對子女財產方面的權利包括財產法上的法定代理權、同意權以及對子女特有財產(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的財產)的管理權{10}673-675。為兼顧兩大法系家庭立法的特點,海牙國際私法會議1996年《父母責任和兒童保護措施的管轄權、法律適用、承認、執行及國際合作公約》則采用了“父母責任”和“兒童保護措施”的措辭,反映了父母子女關系從“父母權利”到“父母責任”理念的轉變。
目前,我國關于親子法的實體規范既不全面,又缺乏可操作性,親子間權利義務關系的規定籠統、簡單,沒有反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影響及要求{12}。父母與子女在人身及財產方面的權利義務分配模糊。[14]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我國涉外父母子女關系的法律適用立法。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涉外親子間權利義務的法律適用規則。[15]面對不斷發生的跨國婚姻中爭奪子女案件以及在國際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的“賀梅案”,當事人和法院都深感我國立法的滯后和亟待完善。在“子女最大利益原則”成為當代各國親子關系法的基本原則時,完善我國親子關系的立法,包括其法律適用法,是確保父母子女的合法權益,促進家庭關系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
《草案》根據我國婚姻法的立法模式,將其分為父母子女人身關系與父母子女財產關系。《草案》第65條規定:“父母子女人身關系,適用其共同住所地法律,或者適用有利于保護弱者利益的一方當事人的本國法律、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第66條規定:“父母子女財產關系適用前條規定,但涉及不動產的,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上述兩條沖突規范分別以“父母子女人身關系”和“父母子女財產關系”作為其“范圍”,采用基本相同的“系屬”--共同屬人法,遵循相同的原則--有利于保護弱者利益原則。其實,父母子女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都是以對子女的利益保護為目的,兩者在內容上很難清晰地區分,例如對子女的法定代理權,即可以體現在父母子女的人身關系中,也可以體現在其財產關系中。因此,在涉外父母子女關系的法律適用方面,我國立法宜粗不宜細,沒有必要區分父母子女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分別制定法律適用規則。
從國際社會來看,父母子女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的立法主要有兩種模式:其一,概括式籠統采用“父母子女間的關系”這一術語,規定一條沖突規范解決其法律適用問題。如《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82條規定:“父母子女間的關系,適應子女的慣常居所地法。如果父母中任何一方在子女的慣常居所地國家均沒有住所,且父母和子女具有同一國家的國籍,則應適用其共同本國法。”2007年日本《法律適用通則法》第32條則規定:“親子間的法律關系,子女的本國法與父親或母親的本國法相同時,依子女的本國法;在其他情況下,適用子女的慣常居所地法。”《立陶宛共和國國際私法》第1.32條規定:“父母子女的人身與財產關系,適用子女的固定住所地國法。父母在子女的固定住所地國無固定住所,而子女與父母雙方具有同一國家國籍的,適用該國籍國法。”其二,將父母對子女的權利義務區分為親權、父母照顧權或監護權,分別制定不同的沖突規則,尤其是對監護制定單獨的法律適用規則。如2004年《比利時國際私法典》第35條規定:“親權、監護權,適用引起確認親權、監護權的事實發生時當事人有慣常居所的國家的法律,慣常居所發生變更時,適用新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親權、監護權的行使,適用權利行使時子女有慣常居所的國家的法律。如果上述所指定的法律不能對請求保護的人或財產提供保護,則適用請求人的本國法。”
雖然立法方式各不相同,但各國有關親子關系的準據法基本是一致的:首先,子女的慣常居所地法是首要的準據法;其次,適用有利于保護子女利益的法律,是選擇親子關系準據法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父母子女間的權利義務問題上,我國宜采用第一種模式。為此,建議直接采用“父母子女之間的法律關系”這一術語,適用同一沖突規范。即“父母子女之間的法律關系,適用其共同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無共同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時,可適用一方當事人的本國法、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法院地法中最有利于保護子女利益的法律。”
五、其他家庭關系的法律適用
結婚、離婚、父母子女關系是家庭法律關系的核心內容。此外,扶養和監護關系也是家庭關系不可或缺的內容,尤其是對扶養和監護采用廣義解釋的國家更是如此。我國對扶養和監護采取廣義說[16],因此涉外家庭關系的立法也包括這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涉外扶養的法律適用
《民法通則》第148條規定:“扶養,適用與被扶養人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對于這一沖突規范在實踐中的運用,《意見》第189條進一步指出,“父母子女相互之間的扶養、夫妻相互之間的扶養以及其他有扶養關系的人之間的扶養,應當適用與被扶養人有最密切聯系國家的法律。扶養人和被扶養人的國籍、住所以及供養被扶養人的財產所在地,均可視為與被扶養人有最密切的關系。”這一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涉外扶養的種類包括父母子女之間的相互扶養、夫妻之間的相互扶養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扶養。對于上述各類涉外扶養義務,法院應根據與被扶養人有最密切聯系的原則,在扶養人與被扶養人的本國法、扶養人與被扶養人的住所地法以及供養財產所在地國家的法律中選擇確定。
《草案》第69條規定:“扶養,適用被扶養人的本國法律、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中對被扶養人最有利的法律。離婚后原配偶之間的扶養,適用離婚的準據法。”該規定沿用了現行立法的方式,沒有區分不同類型的家庭扶養義務,統一適用同一沖突規范去指引準據法。同時,該規定又突破現行立法,不僅明確由法官根據被扶養人的最大利益來選擇適用法律,還對離婚后原配偶之間的扶養作出特別規定。值得肯定的是,對于涉外扶養義務,明確規定適用對“被扶養人有利的法律”這一保護弱者的原則。但對于配偶之間的扶養義務是否有必要規定專門的法律適用規則,應根據我國的司法實踐作進一步考量。
從國際社會有關扶養義務的法律適用立法來看,弱者保護原則日益受到重視。一些國內立法和國際條約都明確規定,扶養義務適用對扶養權利人最有利的法律。例如,《突尼斯國際私法》第51條規定:“扶養義務由權利人的本國法或住所地法支配,或者由義務人的本國法或住所地法支配。法官應適用對權利人最有利的法律。”在國際立法方面,1989年《美洲國家間扶養義務公約》第6條的規定,“扶養義務適用由管轄機關確認的對扶養權利人最有利的法律。”法院必須在扶養權利人和扶養義務人的住所或慣常居所地法律中,選擇對扶養權利人最有利的法律加以適用。2007年海牙《扶養義務法律適用議定書》則對不同類型的跨國扶養義務采取有所區別的法律適用規則。在該議定書中,第3條規定,“扶養應適用扶養權利人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該議定書另有規定的除外;在扶養權利人的慣常居所地變更的情況下,從變更時起適用變更后新的慣常居所地國家的法律。”第4條則規定,父母子女之間的扶養義務,要根據有利于扶養權利人的原則確定應適用的法律。第5條則是規定配偶以及離婚后原配偶之間扶養義務的法律適用規則,首次規定在配偶間的扶養問題上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時還兼顧最密切聯系原則。[17]由于各國扶養義務的種類和程度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海牙《扶養義務法律適用公約》對兒童扶養之外的其他家庭形式的扶養義務都設置一個抗辯條款,允許扶養義務人根據其慣常居所地法或本國法沒有此類扶養義務而拒絕支付撫養費。[18]
我國應借鑒國際社會關于扶養義務法律適用的立法經驗,結合中國的司法實踐,在遵循“有利于被扶養人”原則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司法解釋賦予被扶養人選擇適用法律的權利。此外,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離婚后原配偶之間不存在法定扶養義務,因此沒有必要規定離婚后原配偶之間扶養義務的法律適用規則。同時,對子女扶養之外的其他家庭形式的扶養義務應增加一個抗辯條款,以體現各國法律文化的差異對扶養義務的影響。由此,建議規定如下:“扶養,適用被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本國法、法院地法中對被扶養人最有利的法律。除父母子女之間的扶養義務之外,其他形式的家庭扶養,如果扶養義務人的經常居住地法或扶養當事人的共同本國法沒有規定此種扶養義務時,則扶養人可以主張無扶養義務。”
(二)涉外監護
與涉外扶養問題一樣,我國涉外監護的內涵也與國內民法中監護制度的內涵一致,包括對未成年人監護和對限制或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監護。《民法通則》并沒有規定涉外監護的法律適用規則。《意見》第190條規定:“監護的設立、變更和終止,適用被監護人的本國法律。但被監護人在我國境內有住所的,適用我國的法律。”該司法解釋的適用范圍包括未成年人監護以及限制或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監護問題。但在實務中,涉外監護糾紛主要是兒童監護權糾紛。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上述司法解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缺乏父母子女關系法律適用規則的不足,但在處理我國涉外兒童監護權糾紛時往往難以發揮作用,不能維護我國當事人的利益。
《草案》第70條規定:“監護的設立、變更和終止,適用被監護人的本國法律、住所地法律或者經常居住地法律。”與現行司法解釋相比,該規定是一條無條件選擇性沖突規范。對于涉外監護的設立、變更和終止,可以選擇適用被監護人的本國法、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然而其對被監護人利益給予特殊保護的立法意圖并不明確。從國際社會立法來看,監護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被監護人的利益,因而監護的設立、變更及終止的法律適用應體現對被監護人的特殊保護,即應適用對被監護人最有利的法律。目前,作為體現協調不同法系國家兒童保護(包括監護)措施的國際私法公約--1996年海牙《關于父母責任和保護兒童措施的管轄權、法律適用、承認、執行及合作公約》,在對兒童的人身和財產保護措施方面,采用“兒童的慣常居所地法律”優先適用的原則。[19]對于成年人利益的國際保護問題,2000年海牙《關于成年人國際保護公約》規定,對成年人的保護措施允許通過協議或雙邊行為在被保護人的慣常居所地法、本國法或與被保護的成年人有實質聯系的法律中指定應適用的法律。[20]新近的國際私法立法如《突尼斯國際私法典》第50條、《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85條、《立陶宛共和國國際私法》第1.34條、2005年《保加利亞國際私法法典》第86條等,也都規定優先適用被監護人的慣常居所地法。
筆者認為,對于涉外監護問題,我國應明確采用對被監護人有利的法律的原則,規定:“監護的設立、變更和終止,適用被監護人的住所地法、經常居住地法、本國法中對被監護人最有利的法律。”
附:
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法(建議稿)
第XX條:結婚的要件
結婚的實質要件,適用婚姻締結地法。
結婚的形式要件,符合下列法律之一者,均為有效:(一)婚姻締結地法;(二)當事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三)當事人的本國法。
第XX條:結婚的效力
結婚的效力,適用婚姻締結地法。但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締結婚姻的效力,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社會公共利益。
第XX條:領事婚姻
具有同一國籍的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結婚,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由其所屬國領事依照其所屬國法律辦理結婚。
第XX條:夫妻人身關系
夫妻人身關系,適用其雙方共同住所地法或其共同經常居住地法;無共同住所或經常居住地的,適用其共同的本國法;無共同國籍的,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第XX條:夫妻財產關系
夫妻財產關系,適用當事人協商一致以明示方式在下列法律中選擇的法律:(一)夫妻雙方共同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二)夫妻一方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三)夫妻雙方共同的本國法;(四)夫妻一方的本國法。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適用與婚姻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前兩款的規定涉及不動產的,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夫妻財產關系對夫妻雙方以及第三人的效力,依照夫妻財產關系所適用的法律。
第XX條:離婚
離婚的條件和效力,適用起訴時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第XX條:親子關系的確定
親子關系的確定,適用下列法律中有利于親子關系成立的法律:(一)子女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二)子女出生時的本國法;(三)父母一方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
第XX條:收養
收養成立,適用收養時收養人和被收養人的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法。收養效力,適用收養時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收養終止,適用收養時被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或者適用受理解除收養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第XX條:父母子女關系
父母子女之間的法律關系,適用其共同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無共同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時,可適用一方當事人的本國法、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法院地法中最有利于保護子女利益的法律。
第XX條:扶養
扶養,適用被扶養人的住所地法或經常居住地法、本國法、法院地法中對被扶養人最有利的法律。除父母子女之間的扶養義務之外,其他形式的家庭扶養,如果扶養義務人的經常居住地法或扶養當事人的共同本國法沒有規定此種扶養義務時,則扶養人可以主張無扶養義務。
第XX條:監護
監護的設立、變更和終止,適用被監護人的住所地法、經常居住地法、本國法中對被監護人最有利的法律。
【作者簡介】
汪金蘭(1966-),女,安徽懷寧人,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注釋】
[1]《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已列入全國人大法工委立法計劃,正在討論的草案由“一般規定、民事主體、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婚姻家庭、繼承、附則”等八章組成。其中,第六章“婚姻家庭”包括10個條款(第61-70條),涉及結婚的條件和效力、離婚的條件和效力、夫妻人身關系、夫妻財產關系、父母子女人身關系、父母子女財產關系、非婚生子女的認領、收養、扶養、監護等問題。
[2]從字面理解,婚姻的效力是指婚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即配偶(或夫妻)關系,包括人身及財產兩個方面。只有合法有效的婚姻,才產生法律上預期的配偶或夫妻關系。因此,在外國法上,婚姻的效力大多是指配偶之間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婚姻的效力”一詞則是指“婚姻的有效性”。本文所稱“婚姻的效力”也是特指婚姻的有效性。
[3]《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44條、《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3條,均屬于這種有條件的選擇性沖突規范。
[4]“跛腳婚姻”是指在一個國家有效而在另一個國家無效或者解除的婚姻。由于跛腳婚姻的存在,就可能出現一個人可以在不同國家與兩個以上的配偶維持著所謂“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奇怪現象。這樣勢必違背一個國家的公共秩序、風俗、倫理道德,也使涉外婚姻關系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國際社會應盡量避免“跛腳婚姻”的產生。
[5]我國對屬人法的理解,到底應該堅持本國法主義優先還是住所地法主義優先?對此,《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應該確立一個統一的原則,在以屬人法作為準據法時,其具體的適用順序應保持一致,并將其貫穿到各具體的涉外民事關系之中。筆者主張,我國對屬人法的適用應以“住所地法優先”,這已經體現在《民法通則》第143條、第149條及最高院關于《〈民法通則〉實施意見》第179條、第181條,同時也符合國際社會屬人法立法的趨勢。
[6]根據1978年海牙《婚姻締結和承認婚姻有效公約》第11條的規定,締約國可以拒絕承認婚姻的效力的情形包括:根據被請求國的法律,在結婚時:(1)一方已婚;(2)因血緣或收養形成的一方是另一方的親屬,雙方是直系血親或兄弟姐妹;(3)一方未達法定婚齡;(4)一方缺乏表示同意結婚的能力;(5)一方對結婚沒有自由表示同意(違反結婚意愿)。
[7]如美國《沖突法重述(第二次)》第283條規定:“婚姻符合締結地州規定的要求的,其有效性得為普遍承認,但違反配偶及婚姻與之有最重要聯系的強有力的公共政策者除外。”
[8]大多數國家法律規定:在辦理領事婚姻時,要求結婚當事人雙方都是使、領館所屬國公民,如俄羅斯、比利時、巴西、德國、日本等;也有些國家只要求當事人一方是使、領館所屬國的公民,如澳大利亞、意大利、保加利亞、葡萄牙等。(參見李雙元,金彭年,等.中國國際私法通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31.)
[9]實踐中,我國法院處理國內離婚案件時,將子女撫養、夫妻財產分割問題作為離婚的法律后果一并加以解決。
[10]《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登記辦法》第3條規定:外國人在華收養子女,應當符合中國有關收養法律的規定,并應當符合收養人所在國有關收養法的規定;因收養人所在國法律的規定與中國法律的規定不一致而產生的問題,由兩國政府有關部門協商處理。
[11]央視《新聞1+1》:“中國兒童,世界收養”,2009年11月24日報道(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59078342004342.)。
[12]各國對非婚生子女的定義不一。在我國,非婚同居、無效婚姻、配偶一方與第三者通奸所生的子女,均為非婚生子女。對非婚生子女可以通過男方自認的方式(即自愿認領)成立親子關系;也可以通過親子鑒定的方式(即強制認領)確認親子關系。
[13]德國從1997年底到1998年6月對親子法進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修改。現行《德國民法典》已不再規定非婚生子女的準正制度。(參見:德國民法典[M].鄭沖,賈紅梅,譯.法律出版社,1999:363-367)
[14]根據《婚姻法》的規定,父母子女間的權利義務包括: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第21條)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第22條)。父母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在未成年子女對國家、集體或他人造成損害時,父母有承擔民事責任的義務(第23條)。上述權利義務可以概括為3項:(1)扶養的權利與義務;(2)姓氏決定權;(3)照顧與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此外,父母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還適用《民法通則》中有關未成年人監護的規定。
[15]《民法通則》第148條關于涉外扶養的規定以及《意見》第190條“涉外監護”的規定,是從整個家庭關系的角度來制定的。實踐中.涉外父母子女間的扶養與監護也是按照上述規定處理。
[16]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扶養包括:(1)父母對子女的撫養;(2)子女對父母的贍養;(3)夫妻之間的扶養;(4)祖父母、外祖父母與孫子女、外孫子女之間的扶養;(5)兄姐與弟妹之間的扶養。根據《民法通則》規定,監護制度包括對未成年人的監護和對沒有或限制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監護。
[17]2007年11月23日通過的《扶養義務法律適用的議定書》第5條(有關配偶和離婚后原配偶之間的扶養的特別規則)規定:“配偶之間、離婚后原配偶之間以及婚姻被宣告無效的當事人之間的扶養,如果有一方當事人反對適用第3條的規定(適用扶養權利人的慣常居所地法),則不適用第3條的規定;而在另一個國家特別是他們的共同慣常居所地國家與婚姻有密切聯系的情況下,則應適用該國的法律。”
[18]如1973年海牙《扶養義務法律適用公約》第14條、2007年《海牙扶養義務法律適用議定書》第6條。
[19]Outline of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1996 o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hildren, para. 2. http://www.hcch.net/upload/outline34e.pdf
[20]2000年海牙《關于成年人國際保護公約》第13-15條的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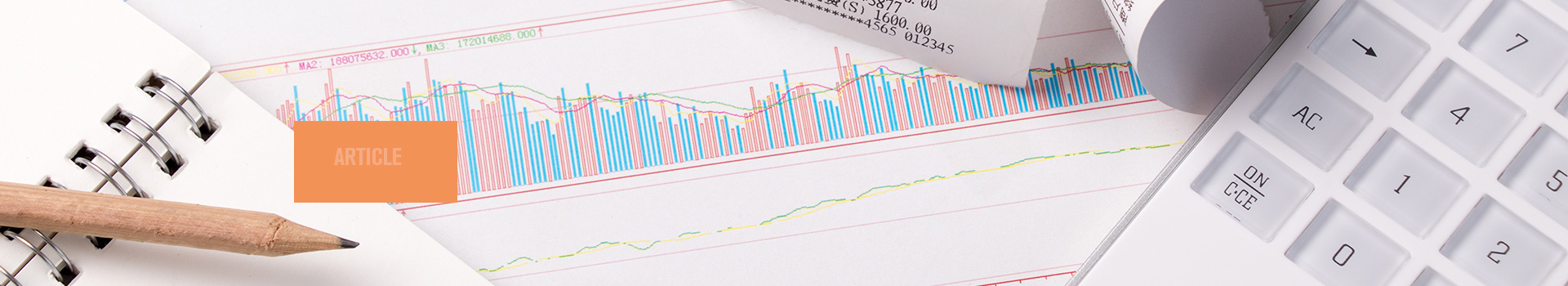
 上海家暢離婚律師網
上海家暢離婚律師網

 滬公網安備:
滬公網安備:

